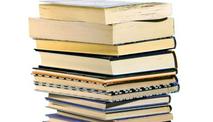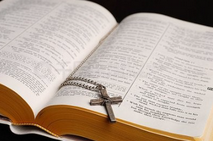这几日读了《中国基督教史》(徐晓鸿主编,中国基督教两会2019年出版),我再次简单地回顾了福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,也感受到了当初宣教士们向中国传福音的热忱和努力。可一想到如今在教会参与侍奉的我们,内心便满是愧疚,实在是太过亏欠。
耶稣会中,第一个踏上中国国土(没有进入中国内地)且死在中国的传教士,名为沙勿略。起初他是要到日本传教的,在当地得知日本的一切文化根源是来自中国,甚至有人对他说:“若是你的宗教是唯一真教,何以中国对此一无所知。”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,于是,他决心去中国传教。可当时明朝的海禁甚严,虽经过多方努力,但只能止步于上川岛,未能到达内地。尽管使命未竟,可他为福音付出的精神却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天主教会,激起了传教士们到中国传教的热情。
当然,在福音传播的历程中,还有很多为了福音甘愿付出的神的仆人们,范礼安、罗明坚、利玛窦等等。这些无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。他们怀揣着对信仰的执着与对灵魂的关怀,不远万里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。范礼安作为耶稣会在东方的巡视官,敏锐察觉到文化差异的阻碍,积极调整传教策略,主张入乡随俗,为后续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奠定了重要基础;罗明坚率先进入中国内地居住,并用中文撰写了第一部天主教教义著作,竭力尝试用中国人能理解的方式传播福音;利玛窦更是深入研习中国文化,与士大夫阶层广泛交往,将西方科学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,成功让福音在士大夫群体中产生影响。他们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与挑战,却始终未曾动摇初心,用生命书写着对信仰的坚守,为福音在中国的扎根与传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可反观今日的我们呢?
有些弟兄姊妹为主、为教会做一点事情就要邀功一般,急于向他人展示自己的“功绩”,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奉献。还有的人、事情没做多少,总是叫苦叫累,觉得不容易。他们在教会的服侍中,常常将个人的得失与回报放在首位,一旦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或赞赏,便容易心生抱怨,甚至对服侍产生懈怠。
这种心态与先辈们默默耕耘、不求回报的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那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,在语言不通、文化隔阂、环境险恶的重重挑战下,尚且能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默默耕耘,我们又怎能因为些许的付出便斤斤计较,因为暂时的辛劳便怨声载道呢?
真正的侍奉并非追求表面的光鲜与他人的称赞,而是源于内心对信仰的赤诚与对使命的担当。这种心态不仅偏离了信仰的本质,更在无形中削弱了侍奉的力量,让原本纯粹的爱心蒙上了功利的尘埃。
有些弟兄姊妹很善于伪装,刻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为主愿意奉献一切的人,但真要为教会做事时,又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。他们往往在言语上表现得极其热忱,时常挂着“为主摆上”“全然奉献”的口号,甚至会主动参与教会的各种分享会,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对信仰的执着。可当教会需要有人承担具体事务,比如探访有需要的弟兄姊妹,或者参与一些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服侍时,他们便会立刻变换面孔。不是说工作太忙抽不开身,就是以家庭事务繁杂为由推脱,要么干脆说自己身体不适需要休养,总能找到看似合情合理的借口来逃避实际的付出。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,不仅让身边的弟兄姊妹感到失望,也让信仰的见证在无形中打了折扣,更让那份本该纯粹的侍奉之心变得虚伪而空洞,失去了信仰应有的真诚。
此外,还有一些弟兄姊妹,虽然参与的侍奉不多,却常常过分在意、比较自己的待遇和补贴。他们会在私下里打听其他同工的补贴是否比自己多,甚至会因为某次活动的纪念品不如预期而心生不满。这种将侍奉与物质回报挂钩的心态,使得原本出于爱心的服侍变了味,仿佛服侍不是出于对信仰的真诚委身,而是一场等价交换的交易。
当眼睛只盯着所得的待遇,心灵便容易被贪婪和比较占据,不仅难以在服侍中体会到付出的喜乐,反而会因为过度计较个人得失而滋生抱怨与不平之气,渐渐偏离了侍奉的初心,也让教会的团契氛围受到了不必要的影响。
今日的侍奉者需要静下心来深刻反思,回望当初那些为主侍奉的先辈们的付出,再对比今日我们的付出,他们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守,不图回报地将身心全然投入,用生命见证着信仰的力量。而我们如今拥有更优渥的环境和更多的资源,却时常在付出中计较个人得失,在顺境中忘记了初心的纯粹。这样的对比,并非否定当下弟兄姊妹们的努力,而是提醒我们应当以先辈为镜,主动剔除侍奉中的功利杂质,重新找回那份因爱而生的热忱与无私。唯有如此,才能让侍奉回归本真,在每一次的付出中彰显信仰的价值,也让我们的心灵在纯粹的服侍中得到真正的满足与成长。
注:本文为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作者系江苏一名传道人。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福音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!